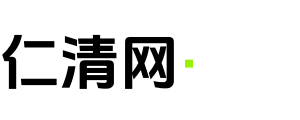六四天安门事件
中国共产党从缔造之初就一直宣扬自己“始终把人民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共产党人与中国人民的感情是“鱼水相依”和“血肉相连”,军队是“人民的军队”,然而,1989年6月4日凌晨,更准确地说,6月3日深夜起,中共命令军队调转枪口,直接对准了毫无装备和毫无防备的普通市民和学生。数百名,数千名学生和市民倒在了“人民的军队”的枪口之下。

对于1989年6月4日的那场血腥镇压以及在此之前的长达50天的学生抗议活动,《中国共产党简史》称之为“政治风波”。《简史》将那场后来几乎由全民参与的民主运动定性为“极少数人” “煽动的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对6月4日当天的屠杀,《简史》说,“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依靠人民”,“于6 月4 日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了北京地区的反革命暴乱”。
《简史》避而不谈的是中共的“果断措施”包括命令“人民军队”动用坦克和机枪,直接对抗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造成无辜民众严重伤亡,给成百上千,甚至上万的中国家庭造成毁灭性打击的事实。对于这场在中国之外的地方被称为“天安门大屠杀”的事件,中国政府非但从未对其罪行承担责任,进行赔偿,反而一直采取各种手段试图掩盖真相,强迫那些受害者和亲历者忘却这段历史。
32年前的今夜,中共动用“人民的军队”屠杀人民;32年后,与“六四”相关的人和事还继续遭受打压。在中国大陆,纪念“六四”的集体活动几乎绝迹,甚至死难者家属的私下祭奠活动也会遭到当局的监视和干预。在香港,这个曾是30年中中国唯一能公开举行集会纪念六四事件的地方,连续两年,纪念“六四”死难者的集会活动被禁止。最近,香港当局更以无牌经营迫使“六四纪念馆”关闭。

那一夜,中共动用机枪和坦克残杀人民
中国共产党从缔造之初就一直宣扬自己“始终把人民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共产党人与中国人民的感情是“鱼水相依”和“血肉相连”,军队是“人民的军队”,然而,1989年6月4日凌晨,更准确地说,6月3日深夜起,中共命令军队调转枪口,直接对准了毫无装备和毫无防备的普通市民和学生。数百名,数千名学生和市民倒在了“人民的军队”的枪口之下。
6月3日晚大约10时,中共当局发布紧急通告,宣布戒严部队将强行清场,并强调,“如遇阻拦,戒严部队可以采取各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从6月3日深夜10时起至6月4日凌晨,荷枪实弹的军队,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武装下,在北京城的大约190多个地段与手无寸铁的学生与市民发生激烈冲突。
根据历史文献学者,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吴仁华的研究,当年中共共调集了19支部队,差不多20万名军人,进驻北京实施“戒严”。这其中包括38军等14个陆军集团军、空降兵第15军、天津警备区的坦克师等。
吴仁华当年亲历了中国军队对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的全过程。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军人开坦克当街杀人。
他在2019年参与美国之音节目时说:“6月4日6点多钟,我与大约3000名的同学撤离到了西长安街的六部口。我们靠在路边行走,当时有三辆天津警备区第一师的坦克发射军用毒气弹,导致北京商学院的一名19岁的女学生龚纪芳因为吸入过多毒气,造成呼吸系统糜烂,后来不幸死亡。 在那个地方,一辆编号106的坦克从后面冲入学生队伍,导致11名学生当场死亡,受伤者更多。”
吴仁华说,正是这段特殊经历促使他后来成为历史学者,专门研究“六四”问题,誓将真相告诉世人。他目前已经完成了三部关于“六四”屠杀真相的著作:《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和《六四事件全程实录》。
1989年,方政是北京体育学院的大四学生,他就是吴仁华提到的“六部口惨案”中的伤者之一。那一天,他的双腿遭到了坦克的碾压。方政告诉美国之音,当时,他跟撤退的天安门广场学生走在西长安街,爆炸的浓烟中冲出坦克,他迅速把一个昏倒的女同学往路边护栏上推,自己却来不及躲避。

六四幸存者、被坦克压断双腿的方政。
方政说:“把她往前一推,自己迫于坦克的压迫感,时间非常短,我就倒到地上,然后就感觉好像一个人 被挤压的感觉,我那时还有点意识,压到了。拖在地下,我整个人咚咚咚颠簸,震动,然后,咚,掉下来了。”
一直以来,中共避重就轻地强调天安门广场范围内无人死亡,但事实上有不少人死在天安门广场。更多的人则死在广场之外,其中西长安街的木樨地、西单路口、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天桥、珠市口和前门一带,以及东长安街的南池子据信是死亡人数和流血最多的地方。
1989年6月4日早晨6点25分,北京国际广播电台的一则消息是这样写的:“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死亡的平民的遗体,摄于1989年6月4日,资料照片
在新闻稿的最后,记者写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这则80秒的新闻据信是唯一一则披露“六四”事件以及痛斥中共当局行径的官方新闻。后来,这则新闻的作者被判刑入狱四年。
由“六四”死难者的母亲组成的“天安门母亲”在“六四”30周年时收集到202名罹难者的相关资料显示,罹难者中年龄最小的仅9岁,最大的66岁。这些人中有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有工人、司机、工程师、厨师、音乐家、复员军人、办公室工作人员等。有一个女儿在去看望丧偶不久、独自在家的母亲时在半路上被打死;一名学生在试图劝解对峙的军民双方时,被军官近距离开枪打死;有些在参加抢救伤员时中弹身亡;有些是在拍摄照片时被戒严士兵开枪打死。
“六四”究竟造成多少人死亡?中共迄今也没有公布具体的死难者名单和伤亡的人数,更谈不上赔偿。
中共公安部1990年7月10日在第五次呈交国务院的报告《有关各地动乱、暴乱中伤亡情况统计资料汇总》说,1989年全国暴乱和动乱期间共有931人死亡,两万两千多人受伤。北京的死亡人数为523人,其中北京学生57人,北京居民45人,外地学生171人,外地职工、居民和农民229人,另有身份不详者21人。
不过,这些数据与其他来源的统计数据有很大的差异。北京红十字会当时的统计大约2千600人死亡,伤者为3万人。后来,英国和美国的解密资料都认为有一万多人被杀。历史文献学者吴仁华对各戒严部队途经地点和北京各家医院的资料进行过搜索和整理后认为,北京红十字会的数据应该最为可信。
邵德廉(Dan Southerland)当年是《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站的站长,他在2014年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六四”发生后,他去了天安门广场并在一家医院看到堆积在那里的尸体。
邵德廉说:“我去了一家医院,要求医生让我进去,我知道这里堆了尸体。这个时候,当局已经开始镇压了并下达了不要让外国人进来的命令,但是这位勇敢的医生说,‘我让他进去。’我进去后看着死尸堆,我意识到,他们的年龄偏大,不可能是学生,他们都是北京的普通市民。所以我们必须记住,在六四事件的死亡者中,最多的是北京市民、工人,而不是学生。”
2004年,因在2003年披露萨斯实情而闻名的军医蒋彦永在向中国全国人大和中央政治局建议为1989年的六四运动正名的信中披露,6月3日当晚,他所在的北京301医院的急诊室从10点多开始到半夜12点的两个小时中,就接收了89位被子弹打伤的人,其中有7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在这封信里,他还提到,很多人被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开花弹”打伤。
在中共的叙事中,1989年学生运动是一场“反革命暴乱”,由于“暴徒”袭击军人,戒严部队不得不进行反击。历史学者吴仁华在研究了六四后中共的有关“共和国卫士”的宣传资料后,认定这是一个谎言,因为戒严部队开枪在前,民众“以暴制暴”在后。
他说:“总共15名戒严部队官兵死亡,其中只有7名因为民众暴力行为造成死亡。官方资料清楚显示了15名官兵的死亡原因、死亡地点和死亡时间,特别时死亡时间,没有一个早于89年6月4号凌晨1点的。而戒严部队军人开枪是在6月3号晚上10点。我找到了第一个死亡民众是宋晓明,他6月3号10点左右在五棵松路口的人行道上中弹死亡。”
抗议学生和民众并不反党,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
关于“六四”的定性,中共《简史》说:这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事实上,绝大部分抗议者,特别是学生,并不希望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也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相反,他们只是希望共产党进一步推进改革,改革弊端。
六四学生运动领袖王丹在2010年曾经写过一篇“假如89民运成功”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八九年的学生从来没有提出取代共产党,我们自己上台的主张,而且不管八九民运最后如何发展,也根本不可能出现所谓学生领袖成为国家领导人这样的事情。”
另一位学运领袖吾尔开希在“六四”25周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当年学生的抗议活动只是希望给中共施压,迫使中共作出良性选择。他说:“全世界所有的群众运动逻辑一样,就是要施加压力,所谓群众集结,就是希望把自己变成一种压力,我们希望向对手施加压力,而且希望对手,就是中国政府,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可以做出良性的选择,就这么简单。世界上的群众运动就是这样的逻辑。”
他还说,八九年的学生运动是“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每一步都给中共当局留下了充分的余地。” 他说,仅存海外的影音资料就可以说明当时学生的诉求绝没有要推翻中共,推翻政府的意图,而中国政府却调动正规军,用坦克用实弹对付手无寸铁和平表达意愿的民众和学生,这个事实无法掩盖,最终有人要为这个事件负责。
1980年代,尽管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角力,经历文革十年禁锢后,中国呈现出一派思想活跃、讨论开放之势。作为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大学生,基本上从1979年开始,每年都会举行游行,中共称之为“学潮”。
在“八九六四”之前,最大的一次学潮是在1986年年底,当时安徽的大学生发动大规模要求民主选举和反贪的示威,示威后来扩散到上海、北京等地高校。中国当局指控那次的学潮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是要企图“否定社会主义”。

孟捷慕(James Mann)当时是《洛杉矶时报》驻北京分社的社长。他2020年告诉美国之音说,当年的学生是爱国的,是富有理想主义的,他们希望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希望限制共产党的权力。
他说:“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体现在为共产党的权力设定新的限制。这也被理解为是爱国主义。那些孩子以及那些支持他们的或是领导他们的知识分子是这么认为的。”
孟捷慕强调说,这些权力限制谈不上是真正拥抱西方的民主和自由。他说,“六四”时期,被视为中共党内改革派的重要人物胡耀邦和赵紫阳也从来没有从民主选举的意义上来谈论民主。
胡耀邦1987年1月,因被中共保守派认为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被被迫辞职。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4月17日,学生们发起对胡耀邦的悼念和示威活动。这被视为是“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开端。
孟捷慕说, “六四”首先是反贪腐、反裙带关系,反共产党当时的所作所为。学生,特别是普通民众,当时对自由和民主的要求是模糊的。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雕像也是在抗议的后期,1989年5月30日才竖立起来的。
在北大学生1989年4月17日提出七点请愿中,没有一点是关于“反党”或是“反社会主义”的。学生们要求重新评价当时刚刚去世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求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公开收入;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等。
1989年4月27日,在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前一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又称“四·二六社论”,将抗议活动定性为“反党动乱”后,北京十几万名学生上街示威,举行了“四·二七”大游行。在游行中,学生们打出的标语是“和平请愿,不是动乱”,“打倒官僚”,“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维护宪法”等。
1989年5月13日学生绝食抗议后也只是提出了两个要求:一个是要求政府迅速与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进行实质性的,具体的真正平等的对话;第二是要求政府为这次学生运动正名,并给予公正评价,肯定这是一场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
1989年5月4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接见亚洲开发银行代表时也说,学生上街游行并不想推翻中共政权。他说: “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
因为公开表示同情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赵紫阳招致了中共当时实际上的领导人邓小平的不满。 “六四”后,赵紫阳被免去党内外一切领导职务,并遭到软禁。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武尔泽(Larry Wortzel)是美国驻华使馆助理陆军武官。他2014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当年拦截军车阻止解放均镇压学生的民众也是爱国和爱政府的,并没有“反党和反社会主义”。
1989年6月2日,武尔泽和同事前往北京西北郊的长城和西山调查当地村民拦下军车,阻止军人进城的情况。当时,武尔泽和同事拍下了军车照片,被解放军军官指责为窃密,并被要求交出胶卷。他说,他本以为与军队对抗的村民会帮助他和同事留下照片,结果,村民们与中国军队站在一起要求他们交出照片。
武尔泽说:“这是让我吃惊的,那些村民们说,如果你所做的一切可能会影响中国的安全的话,那我们希望你们离开,但是,我们希望你们把胶片交给这位军官。最后,我们只好交出了。”

“人民”自始至终与学生站在一起
2021版的简史是这样解释6月4日的屠杀决定的。“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于6 月4 日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了北京地区的反革命暴乱。”
事实上,“人民”并没有站在中共当局的一边,支持镇压。自始至终,人民群众是同情学生并与学生站在一起的。准确地说,这场抗议运动是学生首先发起的,后来获得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响应。1989年4月23日的北京《科技日报》在头版报道学生游行活动,称“学生的行动代表了十亿人民的呼声”。
在这场持续了差不多50天的抗议活动中,教师、知识分子、记者、工人和其他平民等陆陆续续加入进来,全国各地许多城市也先后举行了各类抗议活动。
《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多年后告诉美国之音:“天安门事件很伟大的一点是你看到北京人完全不同的一面。突然之间,出租司机免费搭载学生,学生可以免费坐火车到北京来。我所接触的每一个人都要保护学生,他们排成队,在装甲车前用肉体形成一道人墙。”
在“四二七”大游行的那天,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冲过北京警察、武警以及军队的重重拦阻线,上百万的北京市民,夹道欢迎,站在学生游行队伍的两边,来表达完全支持的立场。
1989年5月13日,抗议学生发动绝食。当绝食学生濒危的画面在电视上播出后,学生抗议活动几乎变成了全民运动。北京的多家医院包括军队的医院自行组织抢救。北京市民、机关单位、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以至武装警察都加入声援、募捐、抢救之中。
1989年5月16日,北京几十万各界民众上街游行声援学生。全国各地还有20多万学生赶来声援。同一天,在包括上海、南京、成都、西安等在内21个城市了5000人以上的示威游行。在这一天,北京1000多名知识分子联署发表了《五一六声明》,声援学生,批评政府也发生对学运的“动乱”定性。在声明中签名的有中国著名的作家巴金、著名诗人艾青、著名学者季羡林等。
5月23日,北京又举行了百万人大游行,不少机关、干部、文化人、科技界、工业界人士加入队伍,喊出让当时的总理李鹏下台的口号。
从5月19日,中共宣布对北京实施戒严后,北京的市民、工人、干部和学生为阻止戒严部队进京,自发赶往各个交通要道,拦阻军人和军车。也有不少民众向军人送水送粮、慰问军人,劝他们放下武器,告诉他们“人民的军队不打人民”。
6月3日上午,在部队得到命令开往天安门广场时,戒严部队的军车在各个主要路口都受到了阻挡,民众在路口设置了重重路障。当晚,即便是官方一再要求北京市民留在家中,仍然有大批市民走上街头阻止部队行进,以保护广场上的学生。没有人相信军队会真正开枪。
当时官方的新闻媒体对六四清场的报道,大部分内容也是同情学生的。除了上文提到的北京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 6月4日当日负责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主持的薛飞、杜宪着一袭黑衣、以沉痛的神态进行播音。此后不久,两名主持人被调离新闻联播节目组。
军队中对戒严也有不同的声音。被调集到北京参与戒严的38军军长徐勤先率先抗命,徐勤先后来被军事法庭判处四年有期徒刑。不幸的是,被剥夺了领导权的38军,后来成了戒严部队中杀人最多的两支队伍中的一支。另一支是空降兵第15军,解放军最精锐的特种部队。

李晓明曾是中国解放军39军116师的一名中尉,也是第一位站出来的“六四”戒严军官。
1989年学生运动期间,李晓明奉命跟随部队从辽宁前往北京负责戒严任务。不过,他说,由于他所在师师长许峰的消极抗命,他们部队在比戒严令所要求的时间晚了整整一天才于6月5日早上到达了天安门广场。
李晓明后来回忆,军队中一些人对戒严的抵抗,早就开始了。在政府颁布戒严令时,有些军官因为不想参加戒严任务或反对强硬对付民众而“在队中表现不好”,令上级把他提前送返原驻地。更有人公开反对戒严并在军中宣传,虽然人数比较少。
李晓明说,他所在的部队早在5月22日就抵达到北京市郊,他清楚记得上级对所有士兵传达过非常明确的指令:“谁要是开第一枪,谁就要对历史负责。”他说,6月3日他所属的军车队以缓速行驶,每当遇到群众堵路就主动停车甚至后退,还得到群众掌声。
六四戒严部队中消极抗命的还有第28军军长何燕然何政委张明春,后来两人都被降级调职。
即便是中共的最高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对是否戒严的态度也是不同的。1989年5月17日,邓小平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和姚依林)提出调用军队,“在北京实施戒严,坚决制止动乱”的提议后,李鹏、姚依林同意,赵紫阳、胡启立反对,乔石中立。后来,邓小平不得不召集顾问委员会,戒严提议才得以通过。
戴晴也是1989年天安门学潮的亲历者,六四镇压后曾入狱近一年。她2014年6月4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发表的《“备忘”六四》说,邓小平的戒严令在从赢得民心、党心和军心上来说,当时遭遇了三个“当头棒”。她说,第一个是《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之后的“四二七”大游行;第二个是在他明确提出要戒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表态,居然多数拒绝紧跟;第三个:王牌军军长(徐勤先)抗命!
“六四”后的镇压和清算持续至今
中共对参与抗议活动的学生和民众的镇压并没有随着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大屠杀的结束而结束。
“六四”之后,当局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和清查,一直延续到1990。在某种意义上,六四的余波一直影响到现在。

1989年6月12日开始,中共当局首先宣布通缉支持学生诉求的,被中共视为“主要煽动者”的方励之夫妇。后来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和李录等21名学运领袖、工人抗议领袖韩东方以及知识分子代表严家其、包遵信等多人也遭到通缉。这些人后来陆续流亡到了海外。
“六四”之后的二十天,也就是1989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正式确认免职赵紫阳、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等人的职务。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被逮捕,鲍彤是六四事件中被捕入狱的最高级别官员。
相对于学生和知识分子,承受了中共最严厉镇压的是被中共称为“六四暴徒”的一群人。这些“六四抗暴者”在89民运期间,在军队进城后,以及“六四”镇压前后,拦截车辆、烧军车、号召市民反抗、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用堵塞交通等各种形式对当局的镇压。他们中多为普通市民。
他们中的有的人被很快枪决,有的人被判处了极其严重的刑期。比如,学运领袖王丹被判刑四年,向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的画像投掷鸡蛋的鲁德成被判处入狱16年。
用《中共简史》中的话来说,“六四”事件促使中国共产党“更加冷静地思考过去、现实和未来”。
这样的思考自然不会包括公布真相,承担责任和进行赔偿。相反,中共还一直采取各种措施试图抹杀有关“六四”的记忆。“六四”屠杀至今仍是中国互联网审查最严密的主题之一;六四死难者家属的悼念活动也会遭到当局的骚扰。这一两年,在香港和澳门的悼念活动也遭到了禁止。中共似乎也达到了目的,现在,中国的年轻一代对三十年多年前北京遭到血腥镇压的民主运动几乎一无所知。
这样的思考还包括强化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更加敌视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六四”拦腰截断了中国社会民主转型的进程。民主、群众示威以及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了中共眼中不可跨越的红线。中共同时还加大了对新闻出版和大众媒体的控制。
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在2019年六四三十周年纪念,在美国之音电视谈话节目中说,中共还从“六四”事件获得了两个政治遗产。“一是开启了暴力维稳的国家治理模式;二是就是坚决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思维,就是底线思维。”
这样的“暴力维稳”和“底线思维”在中共现任领导人习近平的统治下变本加厉。在香港,中共实施《国安法》,一步步打压香港的自由;30年来一直在香港举办的全球最大规模六四纪念活动也被视为禁止。这个月早些时候,香港著名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等四人因去年未经批准参与纪念“六四”集会被法院判处4至10个月有期徒刑。
在新疆,中共对上百万维族人任意拘押,在西藏,中共压制西藏人民的文化和宗教。